|
丝换成白粉,再用唾沫把加工过的烟弄湿,延缓其燃烧速度。 他对吸毒者说自己是画家,拍点照片回去画画用。 他拍过一个叫廖贵英的吸毒女,因为常年吸毒,早已骨瘦如柴,眼神黯淡,如同行尸走肉。 她每天晚上出去卖淫,白天用卖淫赚来的钱买毒品,已经这么过了十几年。 

在这里,两岁的孩子模仿母亲的样子吸烟,身后的母亲,则沉浸在毒品的快感之中。 

在街上随便走一走,都能看到“扎针”的人,装满毒品的注射器,明晃晃暴露在阳光之下。 

为了省下房租买毒品,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,一旦有人“吸死了”,大家就把他抬到山里丢掉。 在瑞丽,卢广拍了十几个胶卷,在最后一天飞一般地逃离了瑞丽。 组照《吸毒者》发表后,卢广获得全国性摄影艺术最高奖项,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。 获奖之后,卢广在新闻摄影圈里引起了极大争议,有人说他在当地与人称兄道弟,转头就把照片发表,为了荣誉和奖金出卖朋友。 但无论如何,那些未曾被人注意过的丑陋,那些总该解决的问题,就这么被更多人看见。 卢广承认,自己一开始拍摄,是为钱。 但拍着拍着,他觉得照相机变成了另一种东西,它用画面说话,直观表现弱势群体的痛苦。 没过多久,一根重若泰山的稻草从天而降,落在放着“真相”的那一端。 自此,天平彻底失衡。 
死亡的味道 完成《淘金者》、《吸毒者》等几个小专题的纪实拍摄后,攒下来的钱花完了,卢广没了“拍摄经费”,回到了老家。 在老家,他靠着商业才能,经营着自己的广告公司。 2001年,当卢广重新回到北京后时,赚来的钱可以在北京购置一套大房子,并且可以支撑他进行几年的拍摄。 一天,他在看报纸,在那些头版头条、家国大事的夹缝中,捕捉到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新闻。 新闻很简单,一个8岁女孩,2岁就患上艾滋病,来北京求医。 可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染上艾滋,这个疑问在卢广心中膨胀。 

通过报社,他找到了女孩的父母,这才知道,在农村,有许多人因为卖血感染上了艾滋。 卢广立刻决定去这里拍摄。 几天之后,河南某个村庄外,一个扛着相机的男人逢人就问“哪里有艾滋病人”,没人理他。 过了两天,他拿着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名单,继续打听,得到的回答却还是“不知道”。 屡屡碰壁的卢广决定“绕路”,问村里的老人们:“你们这里有孤儿吗?我是从北京来帮助孤儿的。” 老人带他见了张夏依。 那年,张夏依12岁,因为没钱已经不上学了。他的卖过血的叔叔、母亲、父亲先后死于艾滋病,3岁的妹妹也没逃过艾滋病魔爪。 他的亲人,只剩下比他大两岁的姐姐,还有79岁的爷爷和78岁的奶奶。 卢广买了书包和课本,掏出210元学费,把孩子送进了学校,张夏依的奶奶特别感激,给卢广煮了一碗面,把张夏依爷爷讨饭讨来的肉都放进去,一定要卢广吃。 张夏依的家庭,是整个村庄的缩影。 整个村将近4000人,95%都感染了艾滋病,当时已有200多人死亡。 

数字只是冰冷的,当卢广深入这个村庄,看到的尽是残酷的现实。 震撼,从呼吸到的第一口空气就开始。 因为艾滋病带来的感染,许多人皮肤溃烂,鲜血和脓水渗出,空气中弥漫着长期没洗澡的恶臭。 那更是死亡的味道。 人们看到村里来了个“拍照的”,觉得卢广能帮他们,纷纷求卢广到自己家里看看。 卢广看到,有许多病人躺在床上,奄奄一息,用微弱的声音呻吟“救救我”,老人抱着他的腿,求他救救她的媳妇、儿子。 连着走了二十多个家庭,卢广一晚上没睡着觉。 “我拍了20多年的照片,从没遇到过这种震撼、痛苦。我一定要拿相机记录它,要告诉大家。”卢广如是说。 通过卢广的镜头,惨烈在光影下显形。 村民被疾病折磨得瘦骨嶙峋。 

艾滋病孤儿的手臂上刻满了“忍”“仇”“杀”等字,眼角一滴泪将坠未坠,他说要杀掉血头,给父母报仇。 

2003年的春节,合家欢聚的日子,13、11岁的两位姐姐,正在准备埋葬自己的弟弟。 弟弟年仅6岁,刚刚死于艾滋病。 

一个老人抱着孙子,向苍天祈求,不要带走她的孙子。 她的儿子和另一个孙子,都已经因为艾滋病死去。 

妻子在艾滋病晚期的丈夫身边掩面大哭,丈夫表情却很安详,或许他早已对这一切麻木。 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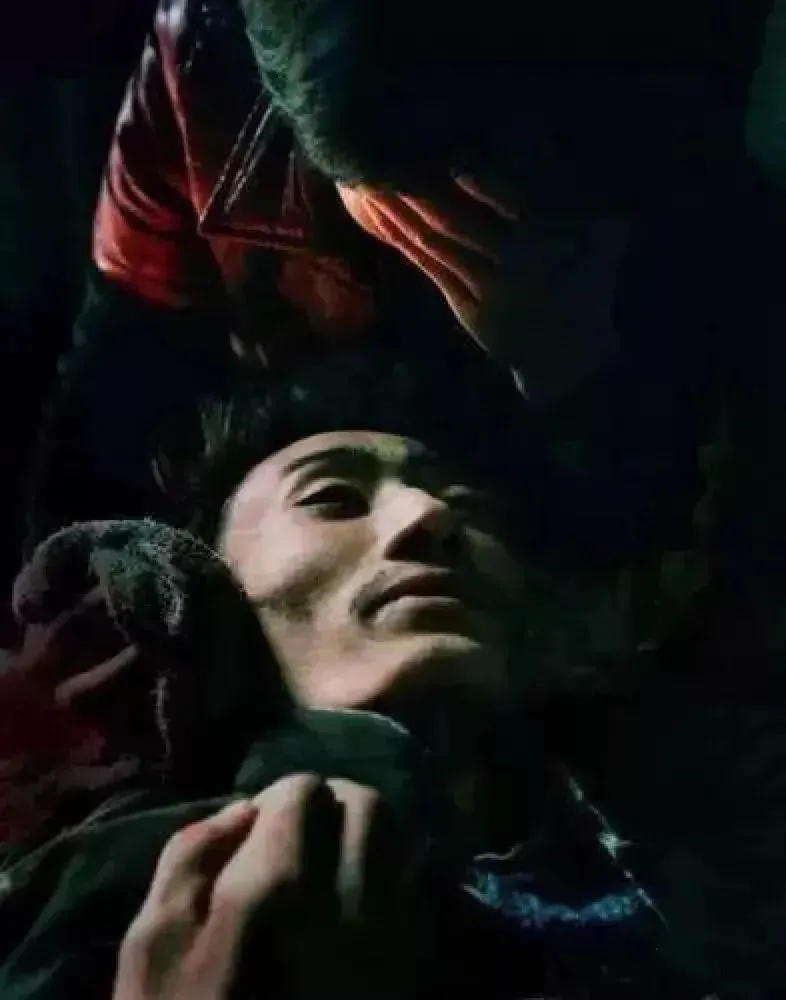
那时,经常有人半夜给卢广打电话,说自己亲人死了,让他来看看。 比艾滋病更难以直视的,是人心。 当地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,尽力遮掩,粉饰太平,甚至以恐吓病人及家属的方式封锁消息。 因为知识的贫乏,许多人把艾滋病人视作洪水猛兽。 当地出产的西瓜,每年都被拒绝收购,运到三四百里外也没人要。 村子周围仿佛筑起高墙,村民被囚禁其中,眼睁睁看着亲朋好友离世,而痛苦在身边不停繁衍。 

在艾滋病村,为逝者送葬的队伍 还好,卢广来了。 两年间,卢广拍了30多次艾滋病村,跑了五六十个村子,胶卷都用了几百个。 人们的目光常常局限在舞台上精心编排的表演,看不到角落里的灰尘。 现在,一阵劲风吹过,灰尘被扬在聚光灯下。 2004年2月,卢广的《艾滋病村》获得了第47届荷赛当代热点类组照一等奖。 一石激起千层浪,河南省领导组织76名干部,和医护人员一起开赴各艾滋病村,展开救助和治疗。 当地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,为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提供治疗药物、免费匿名检测,让孤儿能免费上学,孤寡老人得到照顾。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,亲自探访艾滋病村。 在全国范围内,上亿的资金还有数不清的善款,纷纷流向这个群体,人们也逐渐认识到,艾滋病人没那么可怕。 卢广有二三十个艾滋病村的朋友,他经常接到艾滋病村朋友打来的电话,说他们已经吃上了政府发放的免费药。 在卢广心中,那台天平或许早已不存在。 只有一台相机,永远对准需要帮助的弱者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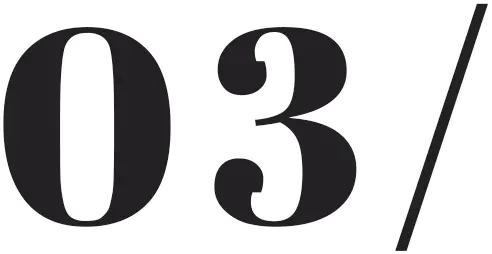
堂吉诃德与风车 小说《堂吉诃德》中,骑士堂吉诃德在向被他想象成巨人的风车发起冲锋前,说道:“即使你们的手比布里亚柔斯(希腊神话人物,据说有五十个头、一百只手)的手还多,也逃脱不了我的惩罚。” 冲锋之后,堂吉诃德的长矛折断,自己被胯下战马摔在地上动弹不得。 被侍从桑丘扶起来后,他没有后悔,而是说:“不过到最后,他的恶毒手腕终究敌不过我的正义之剑。” 完成《艾滋病村》之后,卢广再次拿起相机,向一个庞然大物策马冲锋。 

1995年,乌海市郊的公乌素矿区里遍地都是私人小煤窑,矿工的安全得不到保障,卢广去拍了一回,引起广泛关注,在政府敦促下,小煤窑纷纷关闭。 2005年3月,卢广打算“故地重游”,看看公乌素矿区是否有遗留问题。 但在路上,他发现这里的天空被一股股污浊的黄烟笼罩。 在黄烟的源头,109国道边,一块巨大的牌子耸立,上面写着“欢迎光临中国最大的高耗能工业园”。 这里方圆50里兴建了7个大规模工业园区,园区里大多是高能耗、高污染产业。 沿着公路向前走,卢广遇到一群村民,他们来自附近的北山村。 看到卢广拿着相机,村民都拥过来向他诉苦,有的跪下来求他救命。 他们的村子被工厂环绕,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,晚上睡觉必须关紧门窗,但早上起来,村民脸还是漆黑一片。 从2003年开始,村民里一直有人患上癌症,几乎人人都有呼吸道疾病。 北山村里的小麦产量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,种植的蔬菜和水果也总是出现黑点和腐烂,根本无法销售。 卢广到来时,在距离北山村100米的地方,正在建造一个焦化厂。 卢广拍下10张照片,连同村民们的投诉信,一起寄给国家环保总局,不久,环保总局派了工作小组到当地考察,责令当地政府整改。 

经过协商,工业园区给予村民补偿,北山村村民全部搬走。 但卢广知道,剜去一点腐肉,并不足以祛除巨人身躯上的病症。 自此,他背着相机,踏上了跟踪中国工业污染之路,这条路一走就是五年。 从乌海所处的西部黄河中上游沿岸为起点,卢广的足迹逐渐向中国中部、东部扩展,他走过三大海域和七大河流水系,走过12个省份,拍下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图景。 内蒙古拉僧庙发电厂,两条黑色巨龙遮蔽整个天空。 

在浙江宁波,透过污水管道,可以看到高端楼盘“金色水岸”,但住户们推开窗,只能望见一股浑浊的黑水。 

江苏省常熟市氟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,收集污水却不进行处理,而是用1.5公里长的管道,直接把污水排入长江。 黄色的污水在江面升腾,宛如一朵狰狞的恶之花。 

安徽省慈湖化工园区的地下管道,污水每天从这里排放到长江。 不同化工厂排放出不同颜色的污水,决定江水是什么颜色——黄色、深红色、灰白色,或是黑色。 

宛如末日般的图景下,撼动人心的还是受害者们。 河南安阳钢铁厂附近的一个村子,每天都下“铁雨”,村民在家里用吸铁石一吸,总能吸到铁屑,用手一擦脸,铁屑钻进毛孔里,满脸都是疙瘩。 

黄河被沿河而建的工业园严重污染,一个老汉在黄河边放羊,身后是臭气熏天的污水,不得不用粗糙的手紧紧捂住口鼻。 

长沙湘和化工厂偷排废渣、废水、粉尘,严重污染了当地的土壤,村民捧着漆黑的柚子欲哭无泪。 

广东贵屿镇曾被称为「全球电子废料处理中心」,乌黑的水上漂满垃圾,一位妇女就在这样的水中洗着衣服。 

一个小伙子结婚一年多,就患上了食管癌。 做完手术,他本以为已经痊愈,但开刀一个月后,伤口又长出一个很大的淋巴。 妻子怀孕八个月时,他去世了。 

缺陷婴儿出生率最高的山西,卢广拍下一双畸形的双脚,背景是几名残疾的孩子,坐在破落的墙前。 

为了拍下这些照片,卢广这五年走得坎坷,艰难并不只是来自于翻山越岭。 这个“搞摄影的”牵涉利益实在太大,到哪里都“人人喊打”,被关押、被殴打都是家常便饭。 有官员放话:“一定要捉住卢广”。 甚至有人明码标价,看见卢广来了,举报奖励500元。 为了拍下污染的照片,卢广时常借着夜色或者工厂放哨人换班的间隙靠近污染排放地,但还是总被人发现。 经常被围追堵截,卢广甚至练成一门绝技,在和对方拉扯的几秒钟内,就把胶卷和内存卡“偷天换日”。 一次,他在拍摄灌河排污管道时,一下子冲上来好几个人,把卢广控制住,一通乱打,想要抢夺相机。 卢广死死抱住相机,才没被抢走。 他们打算把卢广用“专人专车”带到了工业园区管委会,但因为要赶在涨潮前埋好管道,对方只留了一个人看守卢广。 卢广在当地的向导把那个人拼命抱住,让卢广逃脱。 向导被抓了起来,被逼问卢广的信息,但他始终没松口,还抽空通知卢广:“你赶快跑吧,他们说一定要抓住你!” 有多少人恨不得置卢广于死地,就有更多的人保护他。 

5年内,卢广数不清自己究竟拍了多少张照片,他从中选了40张,送到国外参赛。 2008年,卢广拍下的《关注中国污染》组照,获得了尤金·史密斯的助研奖。 2009年,他又斩获了尤金·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,那是这一奖项的年度大奖。 无国界医生组织创始人伯纳·库什纳说过:“如果没有照片,屠杀就不存在。” 卢广很喜欢这句话,并改成了自己的版本:“如果没有照片,污染就等于不存在。” 

卢广获奖后不到半个月,由卫生部、环境保护部和新华社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了癌症村张于庄村。 这个村庄之前一直在喝饱含污染物的井水,后来也安装上了自来水管。 当把观察视角拉高,我们能看到许多被污染的地区和企业被通报,责令限期整改。 政府开始反思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路子,各地方相继出台了地方环境保护条例,控制环境污染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点。 巨轮转动,争议仍旧如影随形。 有人认为卢广把国家丑陋的一面公之于众,是为了迎合西方的审美,甚至有人干脆说卢广是拿“家丑”换奖金。 卢广接受采访时,记者问他:“你为什么要去揭开这些伤疤,难道你不爱你的祖国吗?” 卢广说:“正因为爱自己的祖国,我才去曝光这些黑暗面。如果不爱,我管它做什么?”
|